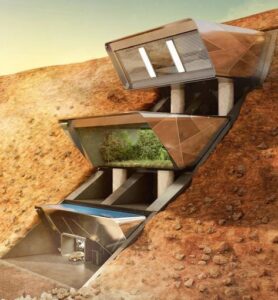稍带甜腻的淡蓝色。
光线打在水面上一圈一圈荡开来,绕着波浪的间隔向前推进。它们沿着直线继续下潜,下潜到深不见底的无垠中。
甜味消失了,随之而来咸涩的铁锈味。蓝光继续乘着波浪在不存在的墙壁上描出波峰谷底,分不清是在俯瞰水面,还是从水中俯瞰虚无。
很难想象这是自称蛾摩拉的人编造的梦境,更难想象这样一个内向的女孩会为自己的接入ID添加蛾摩拉的标识。
我问她那个蓝色是不是取自蓝移,她挠挠手指,有些婴儿肥的脸上挤出一个腼腆的笑容,切伦科夫辐射。
蛾摩拉上周刚到驿宁,她在入境申请的意图一栏上填了旅游,随身行李大包小包多得几乎去哪都要雇移动平台。她说她以前没有来过驿宁,只是在网际播放里看到过,小行星带中有一颗接近球体的岩石块上面有并非是终日漆黑的景色。她觉得自己能在这里获得新的灵感。
我问她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了,她低下头去刘海遮住眼睛,没有,但总会有的。
蛾摩拉是编造梦境的人。
她工作的全称是“官能及联觉体验设计师”,规划好一场梦境中每一丝气味,每一粒光点和每一帧的假象。她跟我解释时我们的咖啡味莫搞被机械臂摆上桌,女孩拿起来喝了一口,“像这种味道太过混杂的设计我们通常是不让过的,平行的体验太多了,只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随后她拿出带在身边的脑机I/O外接组件,问我介不介意她在喝咖啡的时候用这个。我说不介意。
她继续向我解释,他们的创作通常以神经模拟型号的形式存贮并加密好卖给电子脑化后有这种需求的买家,“就像旧时代那些卖画的人一样。”
她说自己很幸运,会用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两种方式写梦,这让她在公司里有不低的地位,因为模拟信号的样式通常只能被电子脑化的人阅读体验,普通人想要尝试这种体验就需要用到非常昂贵的硬件器材。她握紧拳头,保养得当的指甲嵌进肉里,数字信号的官能模拟体验需要换一种思路来写,就像两种计算机语言一样。她替抚养中心的孩子写寓教于乐的童话故事,她替临终关怀中心里排异反应末期的赛博化工薪族写紧张刺激的另种人生。
就我所知,她是他们当中最顶尖的那一批,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
自称蛾摩拉的女孩又喝了一口咖啡,不知道在外接部件中她设定自己喝倒了什么味道。从她的外露的肢体上看不见任何纹身或是赛博化改装的痕迹,发梢整洁眼神清亮像个地球乡间的平凡女孩,让人诧异她为什么用这个名字描述接入星网的自己。
但见过她散播在网上作品的人不会这么说。
她是硫磺与火前的蛾摩拉,有人评论道。
梦境是描述她创作的一种形式,她的崇拜者们似乎更喜欢药物朋克一点的称呼。说到底,编写好的官能体验也包括了快感,认知,情绪感受的拟造,而这些与旧时代的毒品无异。转瞬即逝的星火,刺入骨髓的冰锥,邪神临面的癫疯,她从来不认为那是梦境,而将其当人生真实的一部分。
“我有时候就在想,我们能不能看见可见光外的颜色。”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这些的?”
她看向窗外,小雨从楼栋间飘下,顶空的太阳晕开成一团亮色。蛾摩拉放松身体靠在桌板上,挤压出环绕手臂的红色线条。
“很久以前我们公司接了一个专门关押电子脑犯人监狱的项目,他们有些很有意思的想法。”惨白色的指甲在掌心留下新的划痕,“我是说,非常有意思。他们没有沿用那些放缓时间体验的思路让犯人觉得度日如年,只是给我们一套算法,让我们添一点随便什么好的体验进去,性快感,肾上腺素,反胃,我们加了很多。”
接收项目时,蛾摩拉作为监工体验了一下那个包体。
“非常有意思。”
反复而反复,一切喜怒哀乐在数个纳秒内跳跃回旋,世界融化在苍白当中。
“真的,我觉得我们可以看见可见光外的颜色,但我们不会知道自己看见了。他们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既然可以伪造那一切的悲剧喜剧都没有意义了。”
我把蒜泥面包咽下。
“所以我觉得写什么都无所谓了。既然一切都是大脑的错觉,那么错到什么程度都没有关系。”
她嘿嘿笑起来,跟我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其实不是那些上瘾性极强的色调与快感的混杂。她写过一个干净的梦境,中断语言区与海马体,无需思考一片空白的世界,睡在那里很舒服。
蛾摩拉一边说一边挠着手臂,在肉色上留下一道又一道血红的划痕。
结账的时候她说我来吧,我没有答应。我们在她的旅店前分手,走出几步回头看时,她还再冲我挥手,像个地球乡间的平凡女孩,而不是因为制作精神毒品被通缉的设计师。
只有手臂上血红的抓痕疼痛而真实。
本文作者:驿宁公民 - 克里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