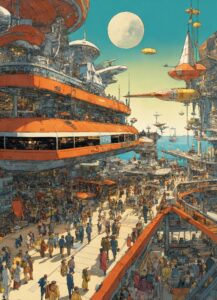2095年10月24日,本该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但在东河对岸雄伟的大楼里,各国代表却像一群学校里的学生,期盼着主席台上领导的讲话赶紧结束。他们中有人要去悉尼赶下一个场子,有人则要到伦敦商讨技术转移的事宜。
在《联合国宪章》生效的第一百五十周年,联合国却走到了它的终点,算是历史老人的一个冷笑话。但在联合地球仰六国集团鼻息的当下,一个致力于国家间平等的组织因何解体,是人类社会早晚要被迫回答的问题。
一、联合国与国联
“联合国”这个词,在23世纪人看来已显陌生。至于其前身“国联”,恐怕只有历史爱好者略有耳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纷纷为工业化时代的战争感到震惊与彷徨——资源消耗和人力需求远超农业时代的任何一场大战。战胜国集团中,英法元气大伤,美国大发横财却依然无法超越旧列强。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战胜国突然发现:下一场大规模战争怕是胜负难料。事实上,当年便有人发出了不详之音:“这不是和平,是二十年的休战”。
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美国总统首先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主张。但诡异的是,当时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凡尔赛条约》,并否决加入国联的提议。这令国联被英法两国所操纵,其核心文件《国联盟约》更规定将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由国联实行委任统治——等于把这些地盘交由英法等国,帮它们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
国联对利比里亚强制劳动制度的解决方法,是“建议由欧洲人或美国人接替这些(管理)事务”。国联认定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却无法推动任何制止其暴行的措施。至于牺牲小国来引导纳粹德国与苏联死斗的种种,更是被视为国联受大国操纵的直接证据。
事实上,国联的议事程序同样漏洞百出:各国皆有一票,但决议需要全体一致投票通过。这种效率低下的议事方式事实上阻碍着任何变革的想法,而维持现状对英法等战胜国最为有利。这更刺激了后进列强“另起炉灶”:意大利和日本都是国联成员,却都在利益得不到满足时悍然退出。
从治理能力看,蒸汽机支撑的工业社会注定只能搭配低水平的全球化——铁甲舰可以轰平港口却不能深入内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注定不可能有真正的全球组织。
国际联盟只存在了二十六年,最终随着二战的烽火化为飞灰。若说联合国从国联身上得到了什么教训,有一点肯定名列前茅:承认某些大国的实际地位,拒绝空想化的绝对平等,是展开国际工作的重要前提。
二、联合国的鼎盛时光
21世纪曾有一款模拟冷战的桌游《Twilight Struggle》,需要玩家将冷战期间的著名事件化为资源或任其发生,以引导美苏中的一国取得胜利。在游戏中,“联合国干预”是一张很有意思的牌:它能搭配对手的事件使用,令玩家获得资源而不触发事件。
和游戏一样,联合国决议对冷战两极同样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和国联一样,联合国同样是战胜国集团惩罚战败国的手段之一。但反法西斯集团对法西斯的惩罚,在任何时候都是众望所归。而考虑到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旧式扩张方式的效率低下与苏联的虎视眈眈,传统西方强国尚且不敢吃相太难看。苏伊士运河危机后,联合国也成为了冷战两极的工具之一——这次危机将英法势力赶出中东,而不掌石油的英法只能乖乖跟在美国后面应声了。
冷战期间所有的大事,都基本离不开联合国的参与。联合国的存在,不但为美苏博弈提供了外交平台,也为美苏压制地区挑战、维护全球秩序提供了白手套——例如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压制新兴强国的议题上密切合作。因此,对于美苏来说,维护联合国的权威符合自身地缘利益——这能极大提升其干涉行动的合法性,从而降低他们维护全球地缘秩序的政治成本。
从议事程序看,抛弃绝对平等主义和维持现状思想的联合国同样拥有巨大的活力。除了在联合国各部门抛弃全票通过并改用简单多数和三分之二多数,安全理事会的设计更是堪称绝妙:理事国共有15个,但其中只有10个需要定期选举轮换。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和苏联永远都有一席之地,并且他们任何一国的否决都能让安理会决议胎死腹中。中国的改换门庭推迟许久才被认可,苏联的轰然倒塌令俄罗斯坐上了宝座,但“首先照顾大国一致”的安理会议事原则从未改变。虽然某些平等主义者对此多有腹诽,但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掌握的武装力量确实让他们手上的选票更显分量。
两级操纵也罢,橡皮图章也罢,联合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柬埔寨和平协定、黎巴嫩人质危机乃至苏军撤出阿富汗,都是在联合国的协调下进行的。或许台面下充斥着肮脏交易,但平等主义的曙光确实在当时的联合国身上渐渐萌发。
三、夕阳西下
与一般大众的印象不同,联合国权威的崩塌并非从伊朗战争开始,其预兆在20世纪末便已显现。道理说起来倒好理解:失去了苏联,美国为什么要照顾那些矮一头的家伙?
1999年3月24日,美国以科索沃人道危机为名,联合北约盟友对南联盟展开空袭。这是北约首次未经联合国授权,对并无威胁的主权国家发动战争。
2002年,伊拉克危机爆发,联合国派遣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检查,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3月18日,美国总统小布什发表电视讲话,要求联合国检查团立即撤离。随后不久,美军开始入侵伊拉克。
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无异于打在联合国脸上的两记耳光。考虑到美国当时远超其他国家的军力,绕开联合国进行军事行动对其而言,不存在实力上的困难。
在安全领域威信扫地的同时,联合国在经济上也不再被视为主要的平台。G8和G20峰会开始不断抢占本属于联合国大会的版面,欧佩克、上合、APEC等组织的频繁亮相进一步挤占了联合国的新闻版面。
当人们回首政治领域,却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如果印度不合作,南亚问题几乎无解;如果伊朗、沙特和土耳其不配合,中东问题将一筹莫展;在东欧和中欧地区,德国的影响力渐渐超过英国和法国;在东南亚,任何绕过东盟的做法都得不到域内国家的有效支持。冷战初期靠美苏就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求助于多个地区大国。而这些地区大国的利益诉求,一直被五大国框架死死地按住。
地缘权力的巨大改变,令战后五大国框架越发显得不合时宜。就算没有后来的剧变,联合国被架空在当时也是可预期的。
四、最后一程
伊朗战争时,联合国调查团因美国的阻挠始终不能组建。而当美国自顾不暇的时候,伊朗战争已经不是联合国能够调停的了。
第六次中东战争期间,虽然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再次受到威胁,但安理会已经无法——哪怕象征性地——派出维和部队。《耶路撒冷共识》与其说是联合国平台的成果,不如说是大国急事从权的唯一方案:暂时没有第二个全球性政治平台来给这样的文件背书了。
而从伊斯兰战争开始,五大国相继陷入自顾不暇的境地,令联合国彻底失去了实际权力。东欧战争令俄罗斯陨落,欧罗巴成立由德国而非法国主导,中美忙于处理内部和周边矛盾,英国被英联邦改组和国内危机所困。至于以色列,则在灭亡边缘挣扎求生,当时连大国都算不上。离开五大国的联合国,其他成员根本无力处理全球问题,只能在自己的区域组织里发声——而没有大国背书的区域组织,又有多大的影响力和实际权力呢?
数据很容易说明问题:第二次美国内战爆发后,联合国办公地点数度变迁,在三十余年中只召开了不到十五次大会。这些大会中几乎看不到全球性议题,而安理会则再没通过一项决议。除了会议地点的多次变更,最大的新闻恐怕是俄罗斯位子的归属——撤掉还是交给斯拉夫。而新俄罗斯改国名为斯拉夫,已经是后来的事情了。
当美联缩回北美,斯拉夫忙于太空建设,欧罗巴对《世界人权宣言》嗤之以鼻时,排除北美和欧洲的联合国已然失去了促进国际合作的能力。随着英国改组英联邦以及伊盟吞并大量西亚和北非国家,联合国的议事机制也面临空前危机——他们在大会到底该有多少票呢?
剧变的波涛渐渐平息时,中国、美联、欧罗巴、英国、斯拉夫和以色列成为事实上的六大国。但他们突然发现:修改联合国条款以改革安理会实在过于繁琐,而进入太空的钥匙根本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掌握。相比全球性议题,搞好区域集团化更有利于他们开发太空。联合国的妥协与斗争,在他们眼中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其他国家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由于美联、欧罗巴、斯拉夫的不合作,五常等于空出了三个。剩下两个想要退出,也只是个手续问题。
五、余波
在六国集团和联合地球组成的人类世界,建立一个全球国家平等参与的政治组织似乎显得荒谬可笑。但现在看来荒谬可笑的想法,却连续两个世纪成为人类追求的目标。
联合国中妥协与斗争的艺术,被六国集团和联合地球所继承。但在六国集团看来,掌握太空的他们根本不必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当差距达到一定程度,连反抗的念头都会自动熄灭。那些想要活下去的国家,只能向六国集团交换空轨使用权、星门配额和形形色色的权益——或者说,乞求。毕竟第一拉动连市场都在安立柯星系而非他们手上,不是吗?
冷战后的联合国与国联相似,阻碍了超级大国和其他新兴强国的地缘利益,其政治权威的不断下降也就难以避免。但第一拉动不可能永恒不变,强如六国集团也迟早要将目光转回人类世界。届时,我们或许能用太阳系的共同平台,祭奠联合国中逝去的美好——在现实基础上,对平等国际社会的不懈追求。
作者:孟阳明
编辑:庄比
图片来源:佚名